煤烟中的生活
发布时间:2019-07-12 09:46:26 作者: 来源:中国保险报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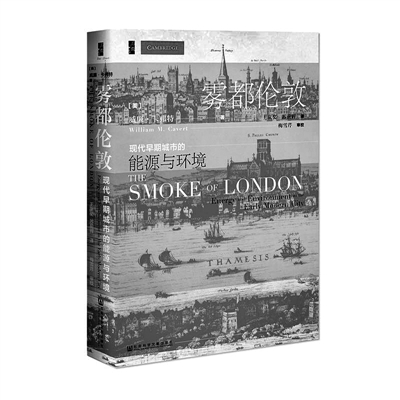
作者:(美)威廉·卡弗特
翻译:王庆奖 苏前辉
出版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时间:2019年5月
定价:69元
□禾刀
1952年12月4日至9日,伦敦遭遇有史以来的“至暗时刻”:大白天的伦敦陷入雾霾笼罩铁幕,犹如一座黑暗之城,短短几天,“超过1.2万人死亡”。
《雾都伦敦: 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》虽以“伦敦雾”为主题的著作,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环保知识。作者威廉·卡弗特长期从事16-18 世纪英国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。经过深入调查后,卡弗特认为,“伦敦雾”的形成不仅是因为技术变革,也缘于社会关系;不仅是因为价格的问题,也涉及政府政策的问题;不仅存在着对污染抵制的现象,也存在着对其接受和漠视的现象。总而言之,伦敦空气被污染的过程涉及政府官员、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,因为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、肮脏的城市环境。
率先到来的“大城市病”
提起“伦敦雾”,许多人立马想到的是煤烟。“大约从1600年开始,伦敦每人每年约消耗一吨煤。”“煤炭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阶级,因为贵族、手工业者和接受救济的人都在购买使用”。不过,此前以木材为主要燃料的英国并没有留下“伦敦雾”记录。一个可信的原因是,伦敦城市发展太快了,以致患上了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“大城市病”。
“伦敦并非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城市,恰恰相反,缔造者为这座城市选择了一个通风良好、拥有海角的河滨,使其居民能够呼吸‘洁净空气’。”此前作为主要燃料的木材,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的太多关注,极可能因为城市体量总体偏小,以伦敦不错的地理条件,自然环境对烟雾的消纳似乎不存在太大困难。
当伦敦人口迅速增长,煤炭使用量随之快速攀升时,人类知识水平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却未能赶上步伐,于是形成了“欠账”。“伦敦从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走过了近1000年历程”,而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,伦敦人口从400万增加到675万。庞大的人口就是一个庞大的基数,在这个庞大的基数面前,小问题也可能因为过于集中而扎堆聚积。
伦敦的“大城市病”并非单纯体现在燃煤的集中排放问题方面。17世纪的伦敦可谓多灾多难,瘟疫与大火交替进行。“詹姆斯一世登基的1603年,瘟疫夺去30000人生命。查理一世1625年登基时,又有40000人死于瘟疫。而1665年的瘟疫,据史学家估计,可能造成80000到100000之间”。而史上闻名的1666年伦敦大火,几乎烧掉了整座城市。
煤烟问题之所以出类拔萃,主因持续时间极长。久而久之,煤炭侵入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,嵌入了伦敦政治、经济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。
“伦敦雾”的本质
自伊丽莎白一世起,数任英国国王均极度反感煤烟问题。伊丽莎白甚至将一批酿酒商送进了监狱,“但是由于煤炭的消费已经深深根植于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和国家权力的观念之中,所以其消费量在整个现代早期以及之后都在持续不断地增长”。
重点考察了英国经济的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写道,如同肥皂、蜡烛、盐和皮革,煤炭也属于“生活必需品”。“必需品”是一种经过长期积累沉淀的生活文化,这种文化不仅是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外化表现,同时也会影响着社会的思维方式。
卡弗特亦认为,“在17世纪和18世纪,煤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伦敦的社会关系,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王国中取得了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地位。伦敦似乎就不能没有煤”。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,一是煤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“刚需”,二是煤炭正深刻影响着伦敦包括决策者和普通居民的思维。
除了居民日常生活需求,酿酒、玻璃制造等均属高耗能企业,对煤炭同样有着巨大的需求。而进入工业革命后,蒸汽机的大量出现,更是大大助推了煤炭消费。伦敦曾试图通过提高税收方式抑制煤炭消费,结果无济于事,反倒遭到包括斯密等人在内的尖锐批评,“伦敦对煤炭所征的税比英国对煤炭出口所征的税更重,这项政策不断被谴责是对外国制造商的滑稽补贴。”
另一方面,自1650年代起,英国与荷兰、法国先后发生多次冲突。至1690年代中叶,“粮食歉收,外战耗资巨大、货币贬值使得英格兰的家庭、公司及整个国家的财务陷入窘境”。加之整个17世纪,伦敦被瘟疫困扰,后又遭遇毁灭式大火……内外交困,必然强化政府对煤炭整个产业链条税收和贸易的依赖。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表明,煤炭也的确“促进和推动了19世纪伟大的技术革新”。
卡尔·波兰尼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实在论学派的创始人。他指出,工业革命兴起,传统商业经济模式无法满足现实要求,因为制造业需要长期投入,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诉求更高。这意味着经济要实现发展,就必须变革传统社会架构,为经济腾出更多话语空间。经济从社会(行政)“压服”状态下“解放”的过程,这就是“脱嵌”。
煤炭的广泛使用,为英国工业革命作出重要铺垫,也为构建近代市场经济打下了基础。从这层意义上讲,“伦敦雾”本质上是英国经济挣脱社会(行政)的“脱嵌”表征,同时也是煤炭作为“生活必需品”,全面嵌入社会的重要节点。
走出“至暗时刻”
直到1980年,伦敦雾霾天气才降到5天以下。从1600年起,伦敦真正走出伦敦雾的“至暗时刻”,前后耗时数百年,足见步履之艰难。
显而易见的是,斯密的《国富论》并未提出环保解决方案。当率先奔向工业社会的英国成为后来者积极效仿的对象时,一并承袭的还有环境污染问题——纵观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,都经历了类似英国“牺牲环境为代价”,先发展后改善的经历。
在“伦敦雾”频频爆发前,“污染”一词尚未诞生。卡弗特认为,伦敦“污染之所以那时才出现,是因为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操纵自然的能力,由此人类开始大规模地破坏环境”。事实上,除了煤烟排放问题,伦敦一度还遭遇了严重的工业废水污染。1878年,因为泰晤士河污染严重,导致640名翻船游客中的大多数人因呛入污水而中毒身亡。
回顾人类近代历史遭遇的重大污染事件不难发现,几乎都是“温水煮青蛙”式改变的结果。一开始人们忙于经济发展,对日益严重的污染现象缺乏足够的警惕,习以为常。虽然伦敦历史上长年遭遇煤烟困扰,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出于各自利益,反倒不怎么希望禁止煤炭贸易。当然,这并不代表人人都愿意接受这种空气,而是有钱人开始在空气更好的郊区建设别墅,隐居乡村。稍差点的则选择偶尔去城外小住。再差点的就只能接受伦敦的现实了。当这些不正常现象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慢慢成为一种日常时,一种扭曲式思维于是应运而生,在伦敦人看来,“有道德的人宁可逃避也不愿改革它”。
今天的伦敦早已送走了的烟雾。作为解读“伦敦雾”样本的重要著作之一,卡弗特的独特之处在于,告诫人们别把污染看成孤立现象。换言之,人类唯有提高警惕,设立并牢牢守住污染侵入社会毛细血管的诸多红线,人类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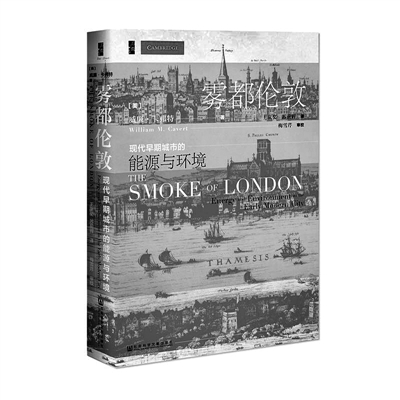
作者:(美)威廉·卡弗特
翻译:王庆奖 苏前辉
出版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时间:2019年5月
定价:69元
□禾刀
1952年12月4日至9日,伦敦遭遇有史以来的“至暗时刻”:大白天的伦敦陷入雾霾笼罩铁幕,犹如一座黑暗之城,短短几天,“超过1.2万人死亡”。
《雾都伦敦: 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》虽以“伦敦雾”为主题的著作,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环保知识。作者威廉·卡弗特长期从事16-18 世纪英国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。经过深入调查后,卡弗特认为,“伦敦雾”的形成不仅是因为技术变革,也缘于社会关系;不仅是因为价格的问题,也涉及政府政策的问题;不仅存在着对污染抵制的现象,也存在着对其接受和漠视的现象。总而言之,伦敦空气被污染的过程涉及政府官员、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,因为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、肮脏的城市环境。
率先到来的“大城市病”
提起“伦敦雾”,许多人立马想到的是煤烟。“大约从1600年开始,伦敦每人每年约消耗一吨煤。”“煤炭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阶级,因为贵族、手工业者和接受救济的人都在购买使用”。不过,此前以木材为主要燃料的英国并没有留下“伦敦雾”记录。一个可信的原因是,伦敦城市发展太快了,以致患上了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“大城市病”。
“伦敦并非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城市,恰恰相反,缔造者为这座城市选择了一个通风良好、拥有海角的河滨,使其居民能够呼吸‘洁净空气’。”此前作为主要燃料的木材,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的太多关注,极可能因为城市体量总体偏小,以伦敦不错的地理条件,自然环境对烟雾的消纳似乎不存在太大困难。
当伦敦人口迅速增长,煤炭使用量随之快速攀升时,人类知识水平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却未能赶上步伐,于是形成了“欠账”。“伦敦从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走过了近1000年历程”,而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,伦敦人口从400万增加到675万。庞大的人口就是一个庞大的基数,在这个庞大的基数面前,小问题也可能因为过于集中而扎堆聚积。
伦敦的“大城市病”并非单纯体现在燃煤的集中排放问题方面。17世纪的伦敦可谓多灾多难,瘟疫与大火交替进行。“詹姆斯一世登基的1603年,瘟疫夺去30000人生命。查理一世1625年登基时,又有40000人死于瘟疫。而1665年的瘟疫,据史学家估计,可能造成80000到100000之间”。而史上闻名的1666年伦敦大火,几乎烧掉了整座城市。
煤烟问题之所以出类拔萃,主因持续时间极长。久而久之,煤炭侵入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,嵌入了伦敦政治、经济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。
“伦敦雾”的本质
自伊丽莎白一世起,数任英国国王均极度反感煤烟问题。伊丽莎白甚至将一批酿酒商送进了监狱,“但是由于煤炭的消费已经深深根植于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和国家权力的观念之中,所以其消费量在整个现代早期以及之后都在持续不断地增长”。
重点考察了英国经济的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写道,如同肥皂、蜡烛、盐和皮革,煤炭也属于“生活必需品”。“必需品”是一种经过长期积累沉淀的生活文化,这种文化不仅是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外化表现,同时也会影响着社会的思维方式。
卡弗特亦认为,“在17世纪和18世纪,煤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伦敦的社会关系,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王国中取得了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地位。伦敦似乎就不能没有煤”。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,一是煤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“刚需”,二是煤炭正深刻影响着伦敦包括决策者和普通居民的思维。
除了居民日常生活需求,酿酒、玻璃制造等均属高耗能企业,对煤炭同样有着巨大的需求。而进入工业革命后,蒸汽机的大量出现,更是大大助推了煤炭消费。伦敦曾试图通过提高税收方式抑制煤炭消费,结果无济于事,反倒遭到包括斯密等人在内的尖锐批评,“伦敦对煤炭所征的税比英国对煤炭出口所征的税更重,这项政策不断被谴责是对外国制造商的滑稽补贴。”
另一方面,自1650年代起,英国与荷兰、法国先后发生多次冲突。至1690年代中叶,“粮食歉收,外战耗资巨大、货币贬值使得英格兰的家庭、公司及整个国家的财务陷入窘境”。加之整个17世纪,伦敦被瘟疫困扰,后又遭遇毁灭式大火……内外交困,必然强化政府对煤炭整个产业链条税收和贸易的依赖。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表明,煤炭也的确“促进和推动了19世纪伟大的技术革新”。
卡尔·波兰尼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实在论学派的创始人。他指出,工业革命兴起,传统商业经济模式无法满足现实要求,因为制造业需要长期投入,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诉求更高。这意味着经济要实现发展,就必须变革传统社会架构,为经济腾出更多话语空间。经济从社会(行政)“压服”状态下“解放”的过程,这就是“脱嵌”。
煤炭的广泛使用,为英国工业革命作出重要铺垫,也为构建近代市场经济打下了基础。从这层意义上讲,“伦敦雾”本质上是英国经济挣脱社会(行政)的“脱嵌”表征,同时也是煤炭作为“生活必需品”,全面嵌入社会的重要节点。
走出“至暗时刻”
直到1980年,伦敦雾霾天气才降到5天以下。从1600年起,伦敦真正走出伦敦雾的“至暗时刻”,前后耗时数百年,足见步履之艰难。
显而易见的是,斯密的《国富论》并未提出环保解决方案。当率先奔向工业社会的英国成为后来者积极效仿的对象时,一并承袭的还有环境污染问题——纵观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,都经历了类似英国“牺牲环境为代价”,先发展后改善的经历。
在“伦敦雾”频频爆发前,“污染”一词尚未诞生。卡弗特认为,伦敦“污染之所以那时才出现,是因为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操纵自然的能力,由此人类开始大规模地破坏环境”。事实上,除了煤烟排放问题,伦敦一度还遭遇了严重的工业废水污染。1878年,因为泰晤士河污染严重,导致640名翻船游客中的大多数人因呛入污水而中毒身亡。
回顾人类近代历史遭遇的重大污染事件不难发现,几乎都是“温水煮青蛙”式改变的结果。一开始人们忙于经济发展,对日益严重的污染现象缺乏足够的警惕,习以为常。虽然伦敦历史上长年遭遇煤烟困扰,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出于各自利益,反倒不怎么希望禁止煤炭贸易。当然,这并不代表人人都愿意接受这种空气,而是有钱人开始在空气更好的郊区建设别墅,隐居乡村。稍差点的则选择偶尔去城外小住。再差点的就只能接受伦敦的现实了。当这些不正常现象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慢慢成为一种日常时,一种扭曲式思维于是应运而生,在伦敦人看来,“有道德的人宁可逃避也不愿改革它”。
今天的伦敦早已送走了的烟雾。作为解读“伦敦雾”样本的重要著作之一,卡弗特的独特之处在于,告诫人们别把污染看成孤立现象。换言之,人类唯有提高警惕,设立并牢牢守住污染侵入社会毛细血管的诸多红线,人类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。




